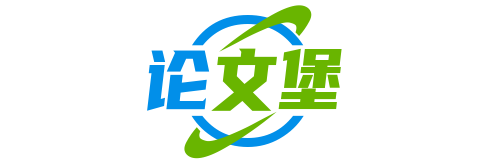抗战时期师陀小说的乡土书写探讨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在抗战的视域下观照师陀小说当中的乡土书写,可以发现,对于师陀来说,乡土书写正是其在“毁家纾难”的现实境遇里的自我疏解的一种方式。正是在经过乡土的涤荡之后,作者才能够更加坚定、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第一章“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乡土书写
第一节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百姓:怀着“耐苦的心”
文学论文怎么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这一事件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导致东北地区渐次沦陷。正是在这国难当头,师陀刚刚从故乡河南来到北平,以“考大学”为名寻找出路。但是实际上,师陀既没有“报名考试”,也尚未“决心从事写作”。但是,不具备职业作家的身份并不妨碍师陀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迅速创作了两个与此事件相关的短篇:《请愿外篇》与《请愿正篇》。这两篇小说正是对“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学生运动所做的记录。在这两篇小说当中,无论是《请愿外篇》当中的群众,还是《请愿正篇》当中的学生,作为这场爱国运动的旁观者与参与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游离于这场运动之外。或者更进一步讲,这场爱国运动表现出的,恰恰是无论群众还是学生都严重缺乏爱国意识。并且,尽管这两篇小说确实存在着作者在后来的一些回忆性文章当中提到的弊端:“文字……受五四的影响,欧化加方言土语,主要是自己缺少运用文字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师陀创作的起步阶段,其作品确实是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作为师陀创作的起点,《请愿外篇》与《请愿正篇》这两篇小说的署名都是芦焚。后来,在作者“决心从事写作”,也就是1933年第二次到北平之后,其继续沿用的也是芦焚这个笔名。而“师陀”则是作者在“芦焚”笔名被盗用之后重新更换的笔名。这实际上已经是40年代之后的事情了。也许在开始创作的当时,作者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擅长类似于《请愿外篇》与《请愿正篇》的创作,因此,笔名为“芦焚”的小说家不再继续此类叙事,而是开启了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乡土书写。并且,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在1937年就与曹禺的剧本《日出》以及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一同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可见其乡土书写的确具有非凡的魅力。
在书写乡土的过程中,师陀频繁写到人物之间的一种对合关系,那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这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多种形态,分为雇主与佃户,男人与女人等。尽管人物的具体身份并非全然相同,但是他们在相互之间共同体现出的正是压迫与受压迫的本质。在雇主与佃户的关系当中,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短篇小说《老包子》。在长工老包子年老体衰“不中用”之后,掌柜丙寅借口老包子弄死了一匹小马,要和老包子算经济上的账,结果便是老包子拿着只得的“七十七吊钱”以及“他的破杂碎”“住到秋二娘搬出去的关帝庙里了”。正是通过算账这种看似公平的方式,师陀写出了一种极致的压迫。最后的这七十七吊钱以及老包子不中用的身体恰似被嗜血吃肉之后又被吐出来的无法消化的骨头。因此,在掌柜丙寅看来是理所应当的算账,实际上正是对老包子的一种压迫。
................................
第二节拿起武器的农民:“挫败的剩余者”
实际上,在抗战前期,师陀不仅写到了战争阴影笼罩下的百姓,还写到了拿起武器的农民。如若说师陀是按照乡土书写的模式来描写抗战小说当中的农民形象,那么,对于拿起武器的农民这一作者既没有实践经历,又无法从其日常生活当中吸收创作灵感的特定角色,师陀更多的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来塑造。然而,想象并不决然只是想象,作者的乡土书写习惯也体现在其中。也就是说,在专门写到“拿起武器的农民”这一特定主体形象的抗战小说当中,还杂糅着诸多乡土的影子。正是在乡土的介入之下,包含“拿起武器的农民”的抗战小说《人在风霜里》、《边沿上》与《三十六个人与一匹马》,呈现出不同于一般抗战小说的别样风貌。
1933年的《人在风霜里》是师陀最早创作的涉及拿起武器的农民的抗战小说。作为一篇抗战小说的主人公,“当了义勇军”的朱连德本应该充满抗战热情,但是他在小说当中体现出来的似乎只有对黑土地的无限渴望与眷恋。在这篇总共十页的小说当中,朱连德与黑土地频繁关联,二者之间持续的联接以不可抵御的态势压倒了小说当中断续的抗战叙事,尽管这被压倒的部分正是一篇抗战小说所应该呈现的主体:
“……甚么时候再回来呀……瞧,那黑的土地,撒上种就会有粮食的黑的土地哟!”他是愚蠢的,也有着愚蠢的观念。
从这些朱连德与黑土地充分关联的引文可以发现,充军并非朱连德所愿,因为正是充军逼迫他离开了黑土地;但是,对于“打走日本小鬼”,朱连德却是真心实意的,因为只有赶走日本人,他才能回到自己日思夜想的黑土地上。显然,在朱连德身上,作为农民的一面要比作为士兵的一面重要得多。然而,仔细观察引文可以发现另一个细节,那就是在朱连德与黑土地的每一处联接,几乎都会出现作者的评判:朱连德是愚蠢的。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本不应该被如此评价,也就是说,作者的这句评判并不是基于热爱土地的朱连德是一个农民的立场,而是对于朱连德所处的正是作者忽视已久的抗战叙事来说的。因为在一篇抗战小说当中,一个士兵如此钟爱土地,念念不忘自己的农民身份,这正是农民愚蠢的体现。然而,作者对士兵“农民式”的描写与强调士兵身份的评判出现了微妙的割裂,换句话说,作者竟然在一篇抗战小说当中极尽刻画一个士兵对土地的深情,却又基于抗战小说的维度对其进行了并不认同的评判。而且,作者的评判永远都是“朱连德是愚蠢的”,这只能显示出其评判的苍白与无力。因此,评判的内容本身又构成对评判的否定。无论如何解释,这种并置的对立都显示出作者态度上的模棱两可。而这正暴露了作者创作抗战小说或者说塑造参战士兵的困惑与矛盾。
..................................
第二章对于全面抗战时代的回应
第一节抗战叙事中农民的再书写
1937年5月,师陀的短篇小说集《谷》获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同年7月7日,七七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就在战火从北向南不断蔓延的时候,师陀逆人流去到上海。此前他与卞之琳在雁荡山住了一段时间。在雁荡山的日子很洒脱,可以洗山间清泉的冷水澡、吃回归自然的人间饭,也偶然会因天降急雨担心出山尚未归来的同伴。但是,从外面传来的报纸送来了战火的消息,惊扰了这两只来此休憩的自在鸟。他们急切地想要回到上海,于是第二天便搭上了返程的班车。但是这趟回程并不顺利,反而充满了狼狈的变数。他们怎样因为一个久矣被卞之琳遗忘在行李中的纸团而被莫名其妙地扣押;又恰巧被偶然的同行者看到师陀在文章上的署名,因此主动作证而解除误会;又遇到从上海逃出的怎样汹涌的人流,差点将他们挤回来时的方向。这些在卞之琳的《话旧成独白:追念师陀》当中都有充满温情的记载。
然而,并非所有现实的残酷都可以以回忆的方式被温情地讲述。回到上海的师陀,被迫直面残酷的战争。当炮火近在咫尺,他是否还能够甚至只是从容地将“从家门前捡来的鸡零狗碎”“编缀起来”?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因为就在全面抗战的初期,师陀写了好几篇有关抗战的小说。它们后来合在一个集子里,叫做《无名氏》。《无名氏》包括一篇《序言》以及五个短篇。这五个短篇分别是《无言者》、《无名氏》、《春之歌》、《夜哨》、《胡子》。
...............................
第二节乡土经验遮蔽下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书写
也许作者自己也意识到,类似于《无名氏》当中的抗战小说,其实正是乡土小说的再生。在这个战浪滔天的时代,仅仅关注农民与乡土,似乎是一种“局限性”的表现。况且,给自己熟悉的书写对象农民附加自己并不熟悉的战事经验,这对作者的创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极易使作者落入先前形成的情感漩涡。而且,挑战的结果是《无名氏》并没有得到认可,反而被批评“这五个短篇是作者的与生活脱节的作品”。因此,这种种因素都导致,在作者之后的创作生涯当中,甚至包括其所在的城市上海沦陷之后,师陀再也没有写过类似的直接以农民为主角并直接表现抗战的小说。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已经放弃了回应时代。实际上,从师陀80年代的回忆性文章当中可以得知,就在1935年12月9日当天,他“还和北京大学的学生一道参加了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显然,这场亲历的爱国学生运动成为全面抗战时期师陀开启新的抗战叙事的契机。并且,也许正是有关这场爱国学生运动的亲身经历,打破了师陀在创作生涯开始时发表的《请愿正篇》与《请愿外篇》当中关于学生运动荒谬不堪的印象。在后来师陀的眼中,“学生是爱国的。”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对于学生运动情感态度的变化促成了作者关于同种类型事件书写内容的改变。并且,《请愿正篇》与《请愿外篇》的写作方式也没有被作者沿用:“这件事是毫不谬误的发生在p城的。这篇只是照实的记录,算不得小说。所以它名为‘外篇’者,因为还有一个‘正篇’,大学生的灵魂是全记在那里的。不久可以写出来,作为本文的姊妹篇,以补其不足。”因为对于此时的师陀来说,“照实的记录”显然已经不能够满足作者的创作意愿,他有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那就是要创作一个有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三部曲。关于这个三部曲,师陀曾经在《师陀自传》当中都提到过:《雪原》(这是应香港《大公报》副刊主编杨刚之约,以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为题材的三部曲,后因香港沦陷于日寇之手,《大公报》停刊,仅写成一部半)……但是其在《师陀谈他的生平和作品》当中又说:“有两点应该更正和说明。
...............................
第三章抗战主题下个人情感的表达
第一节“家族衰败”的回望与书写
师陀其实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含蓄、收敛是他的特点,他很少书写与自身相关的事件,他在文字当中流露出来的情感都是对他人他事的态度。解志熙曾在《芦焚的“一二·九”三部曲及其他》这篇文章当中,通过考察散文《家书——与兰夜》和《牧笛》的版本差异,得出这样的结论:“师陀之所以如此修改……折射出师陀的性格特点,他是个不大愿意自我表露、非常克制感情的人,表露了一星半点,随后就会后悔,于是便动手修改、删节,甚至索性撇弃此类文字。”事实上,这种摒弃有关自身文字的情况在师陀的作品当中并不是特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师陀早期有很多作品记录的都是身边发生的事情。以短篇小说集《里门拾记》和短篇小说《金子》最为典型。在《<里门拾记>序》中,师陀提到,这本小说集是“随手从家门前捡来的鸡零狗碎,编缀起来的货色”。而《金子》,则是作者在北京目睹大学饭馆学徒的命运之后,“为了对北京(扩大一点,当时的全中国)饭馆学徒遭遇的不平”而创作的。尽管这些小说取材于作者的见闻,作者也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态度和情感倾向,但是实际上,在整个的叙述过程中,作者始终都是一个旁观者。也就是说,作者始终都是以超然物外的态度来看待、书写这些事情的。正如杨洪在评论短篇小说集《无名氏》之下的的同名文章时说的:“作者依然没有忘记农民,对农民的爱依然没有丧失,可是业已远离了农民。作者诚然还是同情着农民的,也正只剩着了同情。”钱理群同样提到《无名氏》当中的《胡子》这篇小说:“作者是站在他的对象之外,甚至多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来描写、赞扬他们的。”
第二节个人理想的陷落
..................................
第三节全新的跋涉者形象:“离去——归来——再离去”
..................................................
结语
师陀创作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基本上与抗战重合。并且,无论是抗战前期,还是全面抗战时期,其广受好评的乡土书写,一直都是师陀创作的重点。那么,将师陀小说当中的乡土书写放在抗战视域下进行考察,将会发现,其乡土书写并非对时代的逃避,而恰恰包含了作者对时代的回应。
在抗战前期,师陀的乡土书写主要基于自己的乡土经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成为沦陷区。此时的师陀尽管并没有身处沦陷区直接遭受战争的侵扰。但是,抗战作为时代的主题词,并没有被师陀忽略和遗忘。因此,对黑土地的书写本身就体现了作者对战争的思考。并且,作者对黑土地的书写正是自己乡土经验的再现。
全面抗战时期,师陀被迫卷入战争的漩涡,而乡土仍旧是其写作的主题。此时的师陀对战争有了直接的体验,因此这一时期的乡土书写与抗战前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乡土不再只是过去经验的呈现,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现实的因素。因此,全面抗战时期的乡土书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时代的回应,另一方面则展现出作者抒发自身情绪的现实需要。
因此,在抗战的视域下观照师陀小说当中的乡土书写,可以发现,对于师陀来说,乡土书写正是其在“毁家纾难”的现实境遇里的自我疏解的一种方式。正是在经过乡土的涤荡之后,作者才能够更加坚定、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参考文献(略)
本文收集整理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客服删除!